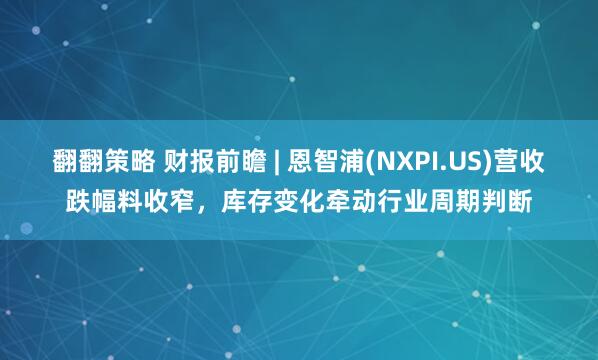杨伯涛在迟暮之年摩根策酪,已经不太认得身边的人了,但是有一句话不但经常说,而且说得字字清楚:“黄维是个外行!”
黄维真是个打仗的外行吗?我们的陈赓大将显然有不同看法,他在阻击并歼灭黄维第十二兵团前,对黄维有一个极其准确的分析和预判,后来发生的事情,恰好证明了《三字兵法》那句话:“知彼知己,百战不殆;不知彼而知己,一胜一负;不知彼,不知己,每战必殆。”
黄维在《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》中多次提到一个地名——南坪集,那就是他命运的转折点:“二十五日(1948年11月25日)夜间,第十八军是夜撤退至双堆集附近集结,第十军在南坪集及其以西之浍河南岸掩护第十八军撤过浍河后,即向双堆集以西地区集结,第十四军在浍河南岸构成阵地,掩护兵团而后之转移,第八十五军之一部位置于南坪集以南,掩护第十军转移。各军上述行动,为解放军发觉。”

黄维的回忆录有一点误区,那就是他的部队调动不是被解放军发觉,而是早在陈赓大将预料之中,并且进行了周密部署,就等这位黄埔一期“老同学”往口袋里钻了。
黄维跟陈赓是黄埔一期同学,但名气远不及陈赓响亮,两人一期毕业后全都被老蒋留校,陈赓当了入伍生上尉连长、步兵科副队长,黄维当了中尉区队长,两人也算半个上下级关系。
陈赓活泼,黄维严谨,两人性格不同,所以陈赓的朋友圈有胡宗南、李铁军、宋希濂,却没有黄维——不知道为什么,黄维被俘前和被俘后的“人缘儿”都不太好,这可能跟他埋头书本不善交际有关。
老蒋对黄维可能也是有一些了解的,所以不停地把黄维送到国内外军校“进修”:黄维在抗战中打过两次硬仗,因为不能随机应变而伤亡惨重——实事求是地说,黄维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打得都很顽强,但那种顽强并不是老蒋需要的。
老蒋想把黄维培养成自己办军校方面的“接班人”,还将黄维字“悟我”改成“培我”摩根策酪,那意思就是让黄维多从事军事教育,为蒋家王朝多培养军事人才。

黄维当过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、第十六期教育处处长,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(南宁分校)主任,“军事委员会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”副总监兼东南分部主任,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,东南干部训练团主任。
老蒋想模仿西点军校办一个“新制军官学校”并任命黄维为校长,黄维选好校址正准备开张,却因为老蒋要平衡何应钦、白崇禧、陈诚、顾祝同的关系,而把他赶鸭子上架,当了第十二兵团司令。
黄维“书呆子气”十足,而且久疏战阵,兵团副司令胡琏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都很不服气。杨伯涛更是对黄维唯老蒋之命是从颇有微词,他在《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》中写道:“黄维之任十二兵团司令官引起内部一片混乱,首先是胡琏没有当上司令官,大为不满;其次是很多干部曾做过黄维的部属,熟知黄维性情孤僻、严峻寡恩,一贯对之不满,这次又来领导,无不灰心丧气。特别因黄维久离部队,对反人民战争是一个外行,害怕断送在他手里。”
在军校讲课和指挥作战是两码事,我们在《亮剑》中看到暂七师师长常乃超给李云龙、丁伟、孔捷在军事学院讲课,不但确有历史原型,而且不止一例:廖耀湘、邱维达、陈颐鼎,据说有六百多被俘和起义将领当过教官,他们的实战水平,当然不如讲台下的“学员”。

黄维还拿在军校那一套管理十二兵团,什么事都自己做主,杨伯涛为此怨气冲天:“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被解放军围困,情况万分危急,蒋介石催促黄维进军打到徐州去,黄等不及吴绍周的到达,下令向北攻击前进。本来是严阵以待,突然变为倾巢出击,这样大的变更计划,黄维不仅没有召集各军长研究一下,就连对同住蒙城内近在咫尺的我事前也没有通知。当我接到行动的命令时感到非常诧异,明知其不可为,但以命令既下,不敢违抗,只好照命令办事。”
黄维什么事都听他蒋校长的,“懂兵法”是他的优点,也是致命弱点,已经与11月23日在南坪集、东坪集严阵以待的陈赓将军(中野第四、九、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、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等组成东集团,由陈赓、谢富治指挥)明确告诉战友们:“黄维要过涡河必定夺桥,南坪集这边只有一座桥能过坦克,我们在这里等他就行了!”
作战会议上有人提出质疑:“如果黄维从别处迂回过去咋办?”摩根策酪
陈赓笑着回忆并分析:“黄维这个人我认识,黄埔一期的,他不是打仗的科班军人,是办教育的,书生气十足,为人比较死板,不像蒋介石别的将领那样圆滑,他不会打破常规,若不首先进攻南坪集,而去进攻别的地方,在他看来,是有悖兵法的,等他进攻失败想转向的时候,就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黄维果然如陈赓将军所料,一头扎向南坪集,然后就悲剧了、麻爪儿了,幸好当时杨伯涛还有点镇静,他建议赶紧离开南坪集:“趁东南面还未发现情况的时候,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,南坪集到固镇只八十多华里,一气就可赶到,一方面取得后方的补给,一方面和李延年兵团合股,再沿津浦线向北打。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作战会议是下午开的,黄维直到午夜才决定采纳杨伯涛的意见开溜,六七个小时就这么白白浪费了,用曹操评价袁绍的话来说,黄维这个人就是“色厉胆薄,好谋无断,见事迟。”
黄维进退失据,在双堆集陷入重围,陈赓将军并不急于发起攻击,为此还向野司建议将总攻时间从11月30日推后三天:“敌人工事非常坚固,不是冲一下就能解决战斗的。现在只能以堑壕对堑壕、以地堡对地堡,四面八方搞土工近迫作业。”
野司回复:“粟裕同志歼灭黄百韬兵团用的也是你说的那种办法,战术问题要根据战场具体情况而定,你的意见是对的,从现在起,西集团、南集团也要搞近迫作业,要推广你的经验,12月5日发起总攻。”

陈赓原本要求三天,野司一下子给了五天,陈赓有了更充足的时间挖堑壕,那一圈又一圈的堑壕,就像一根根绞索,把黄维的十二兵团越勒越紧,黄维算是插翅难逃了。
黄维被俘、特赦,一直没有忘了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陈赓,甚至见到哈工大毕业生王景春也十分亲切:“我跟你们校长是同学,这个人很能干,能打仗,是员武将,难得的人才。平时,他很会做工作,广东东征时,他救过蒋校长的命,校长对他十分器重。后来国共关系破裂,人家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,而我是和他背道而驰,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路。后来,又成了阶下囚。思想起来,十分惭愧。”
其实陈赓在双堆集的时候,也曾写过劝降信,但那封信到了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那里,就没了下文——熊绶春因为惧怕胡琏,而没敢在战场起义投诚。
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,陈赓不但跟黄维是同学,跟熊绶春、胡琏也颇有渊源:胡琏在黄埔四期步兵科一团七连,连长就是陈赓,唐生明也是那个连的。
黄埔三期的王耀武、熊绶春、康泽,四期的文强和林伟俦,见了一期毕业留校当军官的陈赓,都必须立正敬礼,陈赓到功德林看望的,既是“同学”,也是“学生”——王耀武称陈赓为“学长”,还真不是完全合适。

黄维在双堆集输得很不服气,但是知道自己是被陈赓击败,他马上就释然了:“在黄埔军校的时候,我就不如他!”
这还真不是黄维“谦虚”,所有的黄埔军校毕业生,能比得上陈赓的还真很难找,所以第十二兵团不管是黄维当司令,还是胡琏当司令,遇到同学或长官陈赓,也只能甘拜下风。
陈赓对黄维的评价,可以说是精准到了骨头里,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:别说是黄维胡琏,就是胡宗南、李铁军、宋希濂,在战场上遇到陈赓,哪一个不是一败涂地?黄维可能连对面的是陈赓都不知道,或者知道了也没想出对策,您说黄维是不是败得一点都不冤?
配查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